2024-08-31 14:30:19 9
還記得前些年差點就掀起風浪的“南方新浪潮”嗎?
從《路邊野餐》開始。
到接下來的《南方車站的聚會》《小偉》甚至《回南天》,一部接一部地沉浸在南方潮溼的天氣裡,在現實與夢境難分難解的影像中,創造出了一種獨特的南方氣韻。
這樣的風格斷了好久。
如今,冷不丁地又來了一部——
人海同遊
Borrowed Time

導演蔡傑是個新人,可製作班底的其他人卻大有來頭——
監製關錦鵬、配樂雷光夏、藝術指導潘燚森(曾為《天水圍的日與夜》擔任美術設計)。
再加上孫陽、太保、陳湛文的加盟,看起來,應該會有一定的水花?
但事實是——
一。點。都。沒。有。
電影已經上映3天,每天的排片不足1%,總票房僅僅24萬。
可惜嗎?
可惜。
畢竟就新導演的處女作來說,《人海同遊》其實已經給到了我們足夠的驚喜。
尤其是。
我們在這部影片中,看到了難得的——
文學性。
怎麼說?
先聊故事,如果只看影片的情節,其實很俗套。
廣州女孩麥婉婷(林冬萍 飾)因為一起意外事件,勾起塵封已久的記憶。

她想起了她的父親(太保 飾)。
很多年前,她的父親在香港和廣東各有一個家,可是,在廣州生活了十年後,他的父親還是返回了香港,並從此消失在了她們的生活中。
於是。
婚禮前夕,她決定前往香港,尋找這位久別的親人。

老實說。
這樣的故事隨處可見,一個身份不“正當”(小三)的子女,去尋找自己的生父,表面上是尋親,實際上,是尋找自己的身份,為“自我”找到存在的意義。
麥婉婷也是如此。
一個最直接的表現是,在這部電影中,影像風格其實是並不統一的,它逐漸從寫實,向虛幻在轉變。
在最開始廣州的部分。
你可以看到導演努力在追求一種寫實的風格,把角色置於場景之中,力求真實可信。
比如在銀行上班的那場戲。
午休中醒來的麥婉婷幾乎是迷迷糊糊地就撥通了客戶的電話,儼然一個打工人“不得不做”的狀態。
而更重要的。
我們幾乎是第一次看到醒來的麥婉婷額頭上的紅色,那是因為枕著睡覺留下的痕跡。
就像主演林冬萍說的。
導演相當注重背景資料的蒐集,他是讓角色生活在一個環境裡,而非是在一個搭出來的舞臺上表演。
細節相當到位。
而到了香港呢?
颱風天、暴雨夜,影片急轉直下,變得虛實難辨起來。
比如颱風天看投影。
當熱帶雨林的影像灑在斑駁的牆上,你恍惚看到了畢贛在《路邊野餐》裡的那輛火車,有著一種奇異的美感。

更不用說之後突然接到了睡夢中。
他們追尋著食夢貘的蹤跡。

此時,一道陽光像是偷偷地打在二人的身上,那麼耀眼,那麼不可思議。
為什麼會這樣拍?
其實也就是從現實到心理層面轉變的視覺化呈現,意思是說,表面上麥婉婷尋找的是那個拋棄她的生父,但實質上,她試圖補全的是自己內心的空缺。
是的。
相比於電影感(更注重視覺統一),Sir更覺得這裡的文學性要佔據主導作用。
或者說。
導演根本是在用文學的思維在拍電影。
舉例來說。
影片很少會很直白地表達人物的情感,甚至委婉到既不用臺詞,也不用動作。
而是透過——
空鏡。
比如怎麼表達麥婉婷的惆悵?
人物虛化。
重點給到了窗戶上,那些溼噠噠的水珠。

比如說,怎麼傳達麥婉婷在讀到父親的信後,決定去香港尋親的複雜心態?
影片給了整整一分鐘,暴雨中的荔枝樹特寫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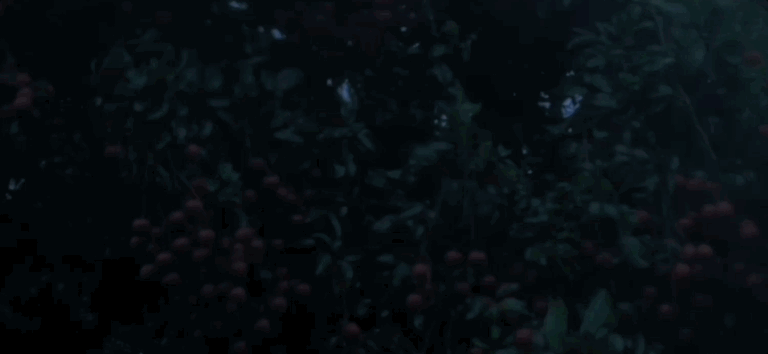
在釋出會上,導演也承認文學對於電影的作用,並把自己偏愛空鏡頭的原因,歸結到閱讀詩詞時,對於景緻的想象。

因為賦比興手法帶來的留白和寫意,傳遞出的是一種不必言明的美,將這種傳統手法變為電影的語言時,空鏡不再只是對環境、背景的資訊補充,它開始輔助情緒的表達。
類似的場景還有很多。
比如用聲音來敘事——
麥婉婷來到香港,見不到她的父親,而去見了一位少年時的學長時,影片並未用隻言片語來講述她的失落情緒,而是讓主角聽了一首南音《魚沉雁杳》。
說的,是音信不同,書信斷絕。

麥婉婷和學長戴著耳機一起聽多年前的一張打口碟,畫面裡的兩人相視一笑,身體也在緩緩搖擺,但觀眾卻始終聽不到男女主耳機裡的音樂,只有斷口的聲音。
說的,又是另一種可無限解讀的情緒。

也是因此。
我們可以認為,這是一部用聲畫來代替講述的電影。
故事本身退居次位。
這樣的做法當然會帶來很大範圍觀眾的不理解(畢竟當下還是故事為王),不過,Sir倒是覺得,這至少是一次成功的嘗試。
畢竟對於新導演來說。
我們看到的應該是其未來的可能性,而非某些方面的瑕疵。
可是,這僅僅是部技術流電影嗎?
當然不止。
文學性之外,其實導演也有著清晰的表達——
雖然影片展現的是麥婉婷的一段短暫旅程,但與此同時,說的也是粵港這二三十年來的變化。
一個證據。
影片的英文片名是“Borrowed Time”,意思是借來的時光。
這個詞是影片中反覆出現的打口CD名,CD代表著麥婉婷的前輩,這張打口碟一借就是許多年。
如今再次重逢,物歸原主。

但同時,它也是父親寫給母親的信:
和你一起的十年,常覺得這些日子好像借回來的一樣,並不是我該過的,現在果然還是要還回去。

什麼意思?
表面上說母親的婚姻是“借來的時光”。
但聯想起父親的身份(香港人),你自然可以清晰地看到,這是這個城市“被借走”與“還回來”的隱喻。
更是廣州與香港的“雙城記”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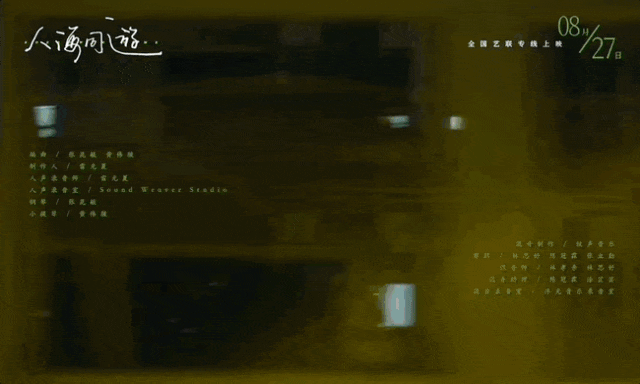
說到這裡,Sir想起影片中,女主母親說的一個故事。
說的是她當年去香港。
在茶餐廳裡,叫了一碗窩蛋牛肉飯,可等飯上來之後,她卻發現沒有蛋。
為什麼?
服務員說,是你沒有早說。
然後女主的母親就哭了起來。
哭的是被騙嗎?
不。
她哭的是自己的白裙子上沾染了醬汁,從此洗不掉了。
這個故事,說的其實就是女主母親的狀態。
因為她沒有往前一步(見到父親的身影后便離開),所以她的生命從此缺了一塊,像一道傷痕,牢牢地刻在那裡,永遠也抹不掉。
而女主呢?
故事的最後,她終於見到了自己的父親,兩人走在香港的街道上,愈行愈遠。
他們說了什麼,其實已經不重要了。
重要的是。
她不再執著於這樣的缺口,不再執著於那些舊日的傷痛。
畢竟。
“穿過那片霧,你就不是原來的那個人。”
人如此,事也如此。

本文圖片來自網路